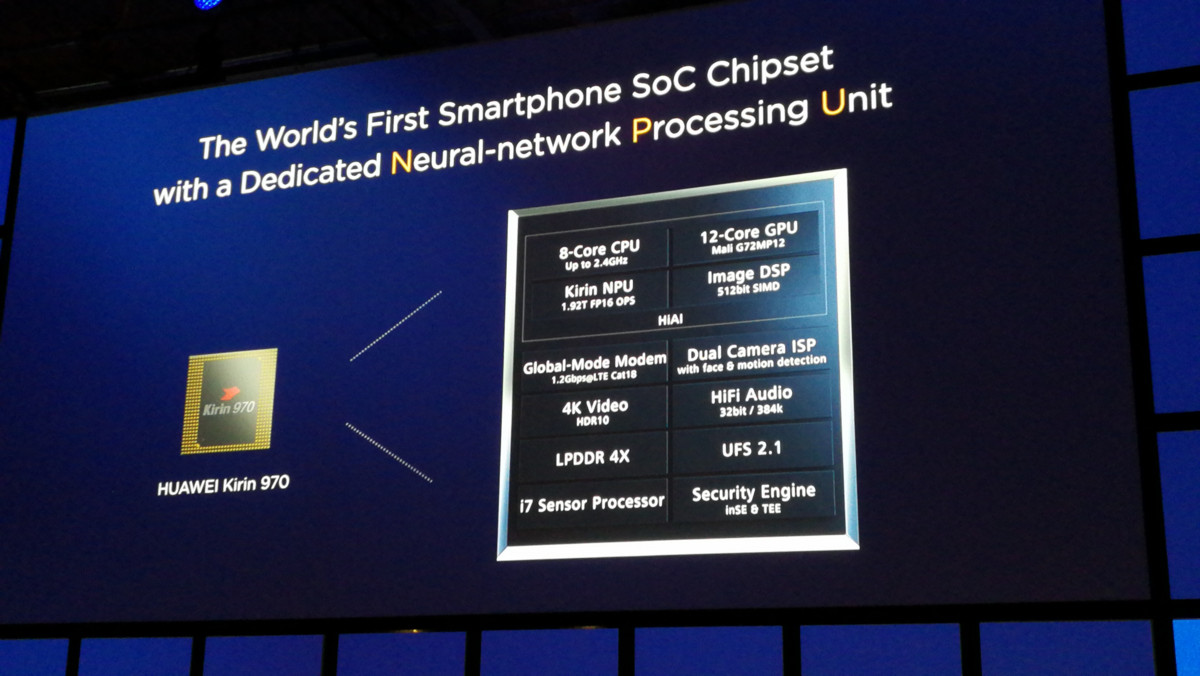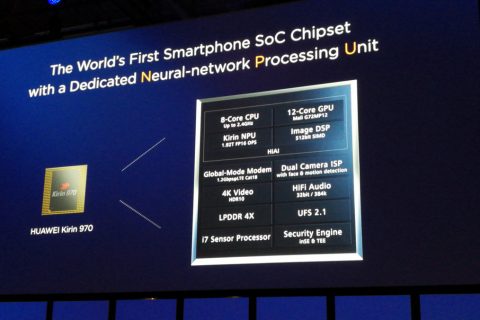作者 焦绪杰 回龙吟(高密)酒业有限公司凤粱红高粱酒创始人
黄浦江的黄昏,水波揉碎了夕阳,将碎金撒在游人的衣襟上。我沿江徐行,忽闻一阵歌声横切过江风:”一人敢走青杀口……见了皇帝不磕头……”那调子粗粝如砂纸,却自有一股蛮力,将四周的汽笛声、谈笑声尽数碾碎。
唱歌的是个肩斜斜的老者,走路时身子颤颤,像棵被虫蛀空的老高粱,偏那歌声却如新酿的烧酒,烈得呛人。他横着嗓子,将每个字都咬出血来。我听出这是《酒神曲》——莫言先生笔下那支从红高粱地里长出来的歌。在上海的钢筋丛林里,这歌声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,突然割开了我记忆的麻袋,高密的红高粱、酒坊的蒸汽、十八里坡的尘土,哗啦啦倾泻而出。
老者与我擦肩时,酒气混着汗味扑面而来。他浑浊的眼珠突然亮了一下,嘴角微微上扬,仿佛认出了某种熟悉的乡音。我驻足聆听,他愈发唱得响亮,这次是”九月九酿新酒,好酒出自咱的手”,唱到”好酒”二字时,他举起虚握的右手,做了个仰脖痛饮的动作,仿佛真有一碗烈酒滚过喉头。
这动作让我想起故乡的老酿酒师。当年在回龙吟酒业初创时,我曾见过那些老师傅们品酒的模样。高粱酒入喉的刹那,他们脖颈上的青筋会突然暴起,像老树的根须扎进皮肉。他们说,酒是粮食的魂,喝下去的不是水,是日头晒过的红高粱,是黑土地里长出来的精气神。此刻江风裹着老者的歌声,将这话语又吹回我耳边。
老者走远了,歌声却如酒曲般在江面发酵。我想起《红高粱》里九儿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的野合,想起罗汉大叔被剥皮时仍挺直的脊梁,想起莫言笔下那些”喝了咱的酒”就敢走青杀口的莽汉。他们身上都有股子蛮劲,像未经驯化的野高粱,在盐碱地里也能蹿得老高。这种生命力,如今在高密的回龙吟酒业里依然沸腾——凤粱红酒的每一滴,都沉淀着红高粱不死的精魂。
江对岸的霓虹次第亮起,将江水染成五色酒液。我忽然觉得,这老者的歌声与眼前的都市奇景竟出奇地和谐。上海需要这样的野性,如同精致的鸡尾酒需要掺一勺烈性的高粱烧。生命的壮美,不正在于这粗粝与精致的交融么?
归途上,我摸出随身带的凤粱红小酒壶,抿了一口。酒液入喉,仿佛有千万株红高粱在我血脉里拔节生长。
附:《闻乡人唱〈酒神曲〉于黄浦江畔》
江风忽送故园声,
蹒跚犹唱青杀行。
肩斜未碍骨中烈,
步颤翻催腔里铿。
红粱已化千盅血,
黑土长养万古情。
莫道申城多软语,
一喉烧酒破升平。